
我沒(méi)有想到我會(huì)得獎(jiǎng),這是意外之喜。我在高校教書(shū)���,寫(xiě)得最多的是學(xué)術(shù)論文,可是我的論文都“有心栽花花不發(fā)”。令人安慰的卻是��,我有感而發(fā)或偶爾為之的文學(xué)性的文字就“無(wú)心插柳柳成蔭”��。所以�,我非常感謝紅色日記征文活動(dòng)主辦者——廣東省文化學(xué)會(huì)頒發(fā)獎(jiǎng)項(xiàng)給我�。這對(duì)我是莫大的肯定與鼓勵(lì)。
古人有以文會(huì)友的說(shuō)法。它道出文學(xué)在我們生活里的重要功能���,就是起相互溝通的橋梁作用��。原來(lái)陌生����、散落各處的人們通過(guò)閱讀�����,彼此會(huì)心�,于是便熟悉起來(lái),有了溝通����,相互切磋,成為朋友�,有了精神的收獲。要以文會(huì)友�����,就首先要有文�;沒(méi)有文,也無(wú)從會(huì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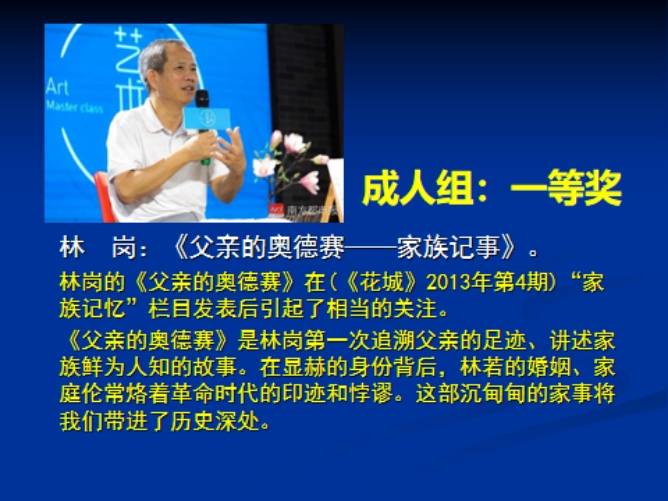 我覺(jué)得���,征文活動(dòng)其實(shí)是把文會(huì)起來(lái)非常好的活動(dòng)方式��。尤其像紅色日記的征文�����,雅俗皆通�����,有廣泛的群眾性�����;上到退休長(zhǎng)者,下到小學(xué)在讀�����,都可以參與����。廣泛的參與性應(yīng)了一句俗話:眾人拾柴火焰高。有了文還不夠,還要文而能會(huì)���。征文評(píng)獎(jiǎng)就是會(huì)的方式�����。
我覺(jué)得���,征文活動(dòng)其實(shí)是把文會(huì)起來(lái)非常好的活動(dòng)方式��。尤其像紅色日記的征文�����,雅俗皆通�����,有廣泛的群眾性�����;上到退休長(zhǎng)者,下到小學(xué)在讀�����,都可以參與����。廣泛的參與性應(yīng)了一句俗話:眾人拾柴火焰高。有了文還不夠,還要文而能會(huì)���。征文評(píng)獎(jiǎng)就是會(huì)的方式�����。
評(píng)出等次固然是題中應(yīng)有��,但這個(gè)題中應(yīng)有的根本精神卻不在等次�����,而在鼓勵(lì)與肯定���。有了肯定,有了鼓勵(lì)�����,自然能推動(dòng)寫(xiě)作的繁榮��,有利于保持初心����,有助于紅色精神深入人心�。
紅色日記征文草創(chuàng)至今已經(jīng)四屆�,參與日眾,影響日廣���,成為眾多征文活動(dòng)的佼佼者�����。最后我衷心祝愿紅色日記征文活動(dòng)越辦越紅火���,越辦越更上層樓。
林 崗
2023年2月18日

林崗在第四屆體育彩票·紅色日記征文大賽頒獎(jiǎng)典禮上發(fā)表獲獎(jiǎng)感言


這是文壇身份最為特殊的一對(duì)父子:父親林若曾是廣東省委書(shū)記���,兒子林崗是中山大學(xué)教授�����?!陡赣H的奧德賽》是林崗第一次追溯父親的足跡����、講述家族鮮為人知的故事�����。在顯赫的身份背后,林若的婚姻��、家庭倫常烙著革命時(shí)代的印跡和悖謬��。
林崗:我對(duì)父親所知甚少
我自從略識(shí)人間事�,記憶里就是一個(gè)缺乏獨(dú)自身份標(biāo)識(shí)的人。出現(xiàn)在社交場(chǎng)合�,換了他人可能有種種頭銜,如經(jīng)理�、董事長(zhǎng)、博士���、教授�、處長(zhǎng)之類(lèi)���,但我不可能����。從小到大�,叔叔、阿姨或朋友�、熟人把我介紹給新認(rèn)識(shí)朋友的時(shí)候�����,一張嘴都是說(shuō):“這是林若的兒子���。”我則含笑點(diǎn)頭��,表示默認(rèn)��。
這經(jīng)歷使我想起了卡夫卡����,與他同病相憐。在他心目中��,他的父親又高又大���,襯得他卑微����、渺小����,必須仰視。盡管他已經(jīng)非常努力擺脫父親“成功人士”的遮蔽����,賣(mài)力證明自己,洗刷人生失敗的恥辱����,但無(wú)論他有多努力,都無(wú)法為世俗所接受���。
我從卡夫卡的命運(yùn)中得到了安慰��,父親的光芒籠罩了我����,盡管這不是他的本意��,無(wú)論我的心里怎樣“抵賴(lài)”���,都不可能改變世人對(duì)于我的外部標(biāo)識(shí)的認(rèn)知��。就拿約稿來(lái)說(shuō)��,《花城》看中的并不是我�����,而是他以及他身邊的一切�����,我的作用在于���,我知道他身邊的一些事兒��,說(shuō)出來(lái)也許有益�,如此而已��。我早早就認(rèn)命了�����。我還不會(huì)走路的時(shí)候�,父親已經(jīng)是東莞縣委書(shū)記;我念大學(xué)的時(shí)候����,父親就是湛江地委書(shū)記;而我還在為自己晉升為助理研究員而得意的時(shí)候,父親已是廣東省委書(shū)記了��。在重視事功和人情人脈的中國(guó)社會(huì)����,難怪別人用父親的所有格來(lái)介紹我���。
不過(guò)我又為我有這樣一位受世人敬重的父親而自豪���。在我的記憶中,各種場(chǎng)合���、數(shù)不清的次數(shù)�����,剛相識(shí)的前輩和同輩���,他們知道我是他兒子的時(shí)候,就當(dāng)面稱(chēng)贊起先父�,稱(chēng)贊他的品行、作風(fēng)�����,稱(chēng)贊他為廣東這片土地做過(guò)的事情。我相信這是真誠(chéng)的贊美�,它不是一個(gè)人、幾個(gè)人孤立的舉動(dòng)���,幾乎是只能用有口皆碑來(lái)形容����。
最感動(dòng)我的一幕出現(xiàn)在父親剛離世的哀悼期間�,海康縣北和鎮(zhèn)潭葛村的村支書(shū)帶了七八位鄉(xiāng)親趕到遠(yuǎn)在廣州的母親家����,吊唁父親。一眾鄉(xiāng)親蹲在院子里�����,那位我素未謀面的村支書(shū)緊緊握著我的手����,連說(shuō)了好幾遍:“我們有今天的生活,全靠林書(shū)記�?��!逼鋵?shí),他已經(jīng)是先父二十世紀(jì)七十年代中期和當(dāng)時(shí)?���?悼h縣長(zhǎng)陳光保在潭葛村試點(diǎn)“包產(chǎn)到戶(hù)”的第三代村支書(shū)了。我心里清楚��,這完全不是先父的英明����,如果沒(méi)有清除“四人幫”���、“文革”結(jié)束��、思想逐漸解放的大背景�,父親就是吃了豹子膽�����,他也不敢做這樣的事情���。
一段幾近四十年前的往事����,依然令相隔一代的鄉(xiāng)親如此動(dòng)情,他們的淳樸也令我為之動(dòng)容�����,我的心里不禁浮現(xiàn)像謎一樣的疑問(wèn):父親究竟是怎樣的一個(gè)人����?過(guò)去我從未想過(guò)類(lèi)似的問(wèn)題,隨著先父的遠(yuǎn)去�����,我自己想弄明白與他相連在一起的往事的念頭�,不時(shí)浮現(xiàn)出來(lái)。我過(guò)去忙于自己的專(zhuān)業(yè)�����,從來(lái)沒(méi)有動(dòng)過(guò)念頭要了解父親走過(guò)的足跡�。即使在他耄耋之年,隨時(shí)都能見(jiàn)到他��,但他對(duì)于我而言���,只是一位慈父�。我對(duì)他依然所知甚少。
(全文刊于《花城》2013年第4期�����,原題為《父親的奧德賽》����,林崗著)

來(lái)源丨《時(shí)代中國(guó)》雜志
總編輯丨何金德